石可,1924年生,字无可,号未了公,又名石之琦。山东诸城舜王街道人。上个世纪30年代末学习版画, 1943年参加中国木刻研究会,金石书画、版本目录之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版画作品曾获第一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优秀作品奖。代表作品有《门》、《鲁难未已》、《孔子生平事迹图》等。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曾获日中文化交流中心颁发的1990年度金奖、新加坡东方哲学所颁发的金奖。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
不论你漫步柳行陶琉市场,还是出入名声不菲的博山陶瓷大观园,或者你沿着205国道张博段绵延80华里的陶瓷一条街浮光掠影地浏览,你一定会发现在林林总总的陶瓷门类中刻瓷作品总是先声夺人,大至数尺黑釉彩刻巨制,小至掌中把玩的玲珑线刻摆件,看画面,有泥古的,有酣畅淋漓的泼墨大写意细腻的,有撒切尔夫人或者邓小平肖像,其质感之强烈,其形神之逼真,乱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我们仍可毫不含糊地说,这就是淄博刻瓷!
屈指算来,淄博刻瓷的发端,距今不过五十余年。五十年中,淄博刻瓷如同梨花万千树,开出浩浩荡荡一夜春风,开得如火如荼,开得铺天盖地,开得炉火纯青!如今,就是随便拣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只要你徜徉于博山窑厂,山头,神头或者大街等街区的民居之中,其家家户户叮叮梆梆的刻瓷之中定是急急切切层层叠叠疾徐交融不绝于耳。好比氤氲着的愉悦心温馨静谧的泉林秋声。
然而追溯淄博刻瓷的渊源,我们就不能不面对那位著名的版画和金石篆刻艺术家石可先生。
许多年前,当“四旧”的余悸还惊颤于样板戏的潦亮之中时,基本赋闲的石可实在不耐寂寞,端详着博山店铺里那些白包的瓷盘,一种也刻凿点什么的冲动抑或灵感怦然而生,他抱回一撂撂的瓷盘,打制了专用的锤、凿、刀,敲响了淄博刻瓷的第一声锤响……一次偶然的机会,石可把他的刻瓷带到了广交会,不想竟受到了舆论的隆重认可。会毕,石可途经上海消作逗留,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结识了长他20岁已届花甲之年的杨铭义,从这位中国第二代刻瓷传人那里学到了有关中国刻瓷方面的很多知识,而且得到不少中国刻瓷艺术源头之作“华铁轩”的创制精品,原来刻瓷的开端竟发轫于清末二位皇帝的驾崩,由於治丧於天下,清廷官窑所产瓷器悉数不许敷彩上色,制瓷业一时萧条起来。一些熟悉陶瓷料性又颇有悟觉的工匠,便试图刻瓷作画,不想此端既开,面世京城,当即为达官贵人看好,就出现了以“华铁轩”为代表的刻瓷艺术,到杨铭义这一代,仍沿用钻石刀,线刻。
似乎齐鲁文化孕育的艺术秉性总是极富挑战性。石可在为“华铁轩”的发轫之作欣喜之余,几乎同时透彻了它的严重不足,用来支撑其全部技巧的只是点和线,而点与线的再完美组合也终不过成就白与黑,这就严重制约了“华铁轩”的艺术表现力。石可毕竟有着深厚的西画功底,必须要有一种突破,让陶瓷上的素色画面立体起来,於是他又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完成这样一种变革:在点、线的前提下增加了面,也就是在黑与白的基础上增加了灰,灰有浓淡,灰有深浅,色块就有了过渡,画面就有了质感,可以说,不知不觉中,中国刻瓷艺术在石可手中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改变。
某年,一个滂沱大雨的夏天,石可在博山访友,被滞留於路长存先生舍下,无聊,遂拿出随身携带的工具,信手摸过泡茶的白色八棱瓷壶,刻了一幅“双清图”,这恐怕是淄博刻瓷传播史上第一幅示范之作。这幅作品曾辗转於高启云手上。
不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淄博陶瓷正酝酿一次规模不小的晋京大展。高启云看了展,讲,山东陶瓷没有刻瓷就没有特色。但当时淄博尚未有人担此重任。尽管石可回青岛前,曾留了一套刻瓷工具给了对琉璃、陶瓷不无钟爱与研究的胡升刚,胡先生除了一天打渔四天晒网地敲打几下外,确曾用心良苦地如法炮制了工具四套,敬送於陶艺名人者四位,但那时则大家都忙於糊口生计,尚无暇顾及更多的艺术追求,二则人们也委实疏於长远考虑,险些与这一新兴陶瓷艺术失之交臂!踌蹰满志的胡先生也终末在淄博刻瓷首席传人的地位上名就功成起来。淄博只好组织朱一圭等一干陶瓷宿将们疾奔青岛取经,石可先生一如既往不吝赐教,且立马组织郑惠民、梁百功、李兴帮等数人加盟,终使淄博陶瓷晋京后名声大噪。随后淄博二度派出张明文等四位再赴青岛,系统地掌握了刻瓷要领,淄博刻瓷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於是马林、冯乃江、李梓源等等名家辈出,不绝於后,便有了梓源先生彪炳於慕尼黑,捧回闪烁辉映的国际博览会金奖。
八十年代末,石可经由博山去济南拜访魏启后先生,邀我同往,一路侃侃,有了以上谈资。
幸甚!轰轰烈烈的淄博刻瓷,由於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由於你无可比拟的入文优势,由於一代大师石可先生由来已久的“淄博情结”导致的情有独钟,你终是发扬了,广大了。在商海汪洋中,你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直至让其他地市的刻瓷兵团彻底偃旗息鼓!然而也有人这样讲,庆幸之余,又有加倍的扼腕之惜在里头啊,淄博刻瓷已是一哄而上,泛滥成灾,这就不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虽埠外产品不敢匹敌,但淄博出品价值亦是共贬再贬,其总体品位,甚至早已远离当年的水准,云云,兴许只能见仁见智了,只是不知年已古稀的石可先生故地重游,耳听密匝匝好一片“叮叮梆梆”刻瓷之声,该作何种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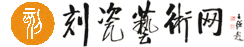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