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刻刀、一把錾子、一方木槌,在莹如玉、薄如纸的瓷器釉面碰撞出清脆的声响,轻轻凿画出一道道或深或浅的线条,上色后,呈现国画独有的皴染效果……这便是被誉为“瓷器上刺绣”的北京刻瓷。作为这项市级非遗项目的第三代传承人,陈永昌已经默默坚守了59个年头。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期待能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让传统手艺重放光彩。
刻瓷传人陈永昌
入行
先练刻线
一刻就是一个月
陈永昌作品姊妹篇《幸福路》与《天路》
在陈永昌的家中,一排棕红色边框的玻璃展示柜几乎占去了整整一面墙,原本就不宽敞的客厅显得格外局促。“右边是陈老师的刻瓷,左边是我的面人。”同样是工艺美术大师的老伴儿郎志丽乐呵呵地介绍着,“我们俩从五十年代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没离开这些,平时做完了互相给看看,提提意见。”
郎志丽口中的“陈老师”虽已是满头华发,但聊起刻瓷来神采奕奕。“我入这行得从父亲说起,他是我的恩师。”据陈永昌回忆,1904年,时年15岁的父亲陈智光因家贫而辍学,家里人希望他能学点手艺。恰逢清末光绪年间,顺天府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设立工艺学堂,陈智光便成为其中刻瓷科的学员,“那时候专门从上海请来著名刻瓷艺人华约三当老师,学员一共二十多个。三年学徒期满后,这些人大多各奔他乡,只有我父亲和朱友麟留在了北京。”
两位老前辈对刻瓷工艺进行了改革,将南方惯用的“刻”和北方常用的“錾”相结合,形成“北京刻瓷”自成一派的风格。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一直在前门西河沿一家瓷器店里“打工”,专攻老本行刻瓷。
“我父亲以工笔为主,朱友麟则擅长写意,哥俩本想着要在刻瓷这一行当里闯出个名堂,可无奈后来活儿不多,只好暂时转行,父亲改做牙雕,朱友麟从事刻章。”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陈永昌感慨良多,“所幸解放以后,国家授予他们‘老艺人’的称号,并安排在成立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这才有了转机。”
1957年,16岁的陈永昌子承父业,以学徒工的身份开始在研究所跟随父亲学习刻瓷。“虽说小时候经常看父亲做,但一直没上过手,毕竟瓷器易碎又金贵,一旦弄坏损失可就大了。”陈永昌清楚地记得,学徒生涯的起步枯燥而漫长,“父亲给我一把刻刀,一个瓷制的笔筒,先练刻线,一刻就是一个月,得刻直了才行。”
陈永昌发现,刻瓷远比想象中来得复杂,“只要拿起刻刀,就要保证精神高度集中,手指和手腕要配合起来用力。刻线不能轻易下笔,得沉得住气,切忌操之过急。力道轻了不着痕迹,重了又会伤及瓷胎,好端端的一件瓷器就可能成了废品。”
就这样,陈永昌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退休离开之前,从来没有上过市场,做完的东西都归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作为礼品赠送,对行情始终没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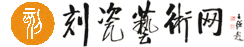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