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 2005 年秋,我在采访我校建筑城规学院的一个学生展览,跟美术系系主任张奇老师聊天,他向我提起说学院里一个老师的雕塑作品刚刚获得全国陶艺设计创新评比铜奖,值得报道,并热心向我引荐刘秀兰老师。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刘老师从走廊的另外一头向我走来,端庄美丽,步履轻盈,长长的卷发一颤一颤的,一如故人重逢一样的亲切。一开口,那带有潮汕味的普通话,令人印象深刻。
不久后我受邀去刘老师家中,不大的客厅全是她各个时期的作品,沙发旁、电视机柜旁、拐角处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泥塑,沉浸于暗薄的灯光下,各自表情,低沉不语。“这是米儿,这是高士。”她一件件向我介绍,用手轻轻抚摸,那褐红的泥身,轻扬的衣袂,在她的爱抚下泛出温柔的微微光亮。
观其早期作品,“魂”“达摩”“高士”,还是以传统雕塑为主,待到“米儿”“宫女”和她的古意人物系列,她的风格已经确立:跳出传统的雕塑塑造手法,用泥片的卷曲黏合塑造人物形态。她在雕塑和陶艺之间寻找到一个结合点,充分挖掘泥质的情感表达。泥片有很好的柔性、延展性和可塑性,最大程度地强调了雕塑的扩张性和饱满感。泥的柔软制造出线条的流动,泥干后进窑,自然流畅的感觉烘托而成。让我想起整个中国美术史中,笔法和线条一直是最重要的品评标准之一。

《达摩》

《小米儿》

《伴奏者》
无论书法、绘画,甚至是雕塑,早期汉砖像所运用的纾缓笔法,与书法的不同仅在简略而已。不用说,科班出身的刘秀兰老师经过传统文化艺术熏陶,同时又有扎实地造型基础训练,才能让线条自由流动,从而把人物造型带入“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她的人物造型是静态的,但却在宁静之中聚积了某种动势,人物的眉眼、嘴唇、忽粗忽细的线条活泼生动,所有的人物好像共同摇晃在一阵古典韵律之中。东晋顾恺之在论画时引用嵇康的诗句,他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意思是涉及人物的精神活动,尤其眼神的表达,是需要“点睛”之笔的。在“肖像系列”“宫女系列”“米儿系列”“淑女”“艺术家”系列中,人物的眼睛刻画是那样特别:有时是细细浅浅的一根线,有时是细小的眼缝中嵌上浅色的陶土,有时只是朦朦胧胧的隆起,并没有实体的眼睛,只留出眼睑的轮廓,激发观者的想象。那微微张开的唇,像是用刻刀精细描上的,诉说着若有若无的思念;而鼻子和下巴,常常呈现出一些泥巴入窑后自然的开裂,与光滑的肌肤表面呈现出有趣的对比。结合泥片特征塑造的人物的衣纹,头发的弯曲,与人物整体气质相得益彰,呈现出语言表达与思想情感的高度统一,然而她的手法却是轻松而自然的,真是太考验功夫了。

《花季》

《陆羽》
我想,这一切美的表达源自于她对生活的热爱。作为女性艺术家,总是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情感荷载。记得她曾经对我说,她全身心投入的艺术生命开始地比较晚,等到孩子长大,出国留学,自己才有多一点的时间从事创作。“都快 40 岁了,才真正有时间心无旁骛投入创作。”她感叹时间的飞逝,对创作生命倍加珍惜。建筑城规学院 C 楼 3 楼 10 平方不到的工作室内,她日以继夜地埋头创作。沉浸于艺术,以泥土为伴,她一下子找到了生命能量的释放:用磅礴情感赋予手中人物以生命,以神采,诉说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
雕塑陶艺制作工艺复杂,不好拉坯,泥土厚重,费力费时又辛苦,制作一件完整的作品,从构思、打稿、制作到最后烧制往往要几个月的时间。陶土的干湿度和气候变化对作品创作影响很大,很多时候上午打好的泥下午就不能用,烧窑的火候也要掌握好,否则报废率也会很高。人物创作和刻画最难表现,就像绘画中的大写意一样,泥片起落,线条的游走不合心意,整个雕塑推倒重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推到重来,才会有最后完整的造型。经过一番泥与火的蜕变,一件件作品如同她的孩子,寄托着母亲对孩子的浓情厚意。
刘老师爱美,每次见面,她总是精心着装,品位不俗,具有艺术家气质。她也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并善于发现美,无论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照相机。记得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看戏,看戏间隙,在灯火璀璨的上海大剧院内,观众们都在合影留念,她却对着各种海报和摆件拍来拍去,我不解,她说:“你瞧这个人的唇角,那样的一抹微笑,多像蒙娜丽莎。你看她的姿态,多有趣。”原来她是为自己的创作在寻找素材。
过往的生活塑造了现在的自己。唯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砺而白云出岫,才能不负本心,不负年华。生活打磨了她,让她十年的艺术创作始终是那样的投入与热爱。她走出了一条艺术家特有的道路——用作品向过往的生命、自然的天地致敬,用心灵拥吻大地,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她,容颜依旧,一如她手塑的人物:自信昂扬,精神焕发。(文/李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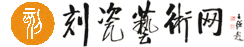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