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山这个名字很少听闻,可是全国寺庙的神佛雕像几乎都来自这条太湖边上小渔村。冲州的百来户人家祖祖辈辈都在传承佛雕手艺,从家庭的小作坊到现在满街的工厂。
走过牌坊就能闻到淡淡的樟木香,听到叮叮咚咚的敲凿声。湖岸边上、草丛里、小院里到处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佛像。生意好的时候,佛像比村里的人还多。


冲山的佛像是活的。都说女娲仿照自己用泥土捏出了人,吹了一口仙气泥人就活过来了。佛雕恰好相反。冲山的匠人把心中的众生相刻出了佛像,匠心赋予了佛像一种人的灵性。

佛雕这个行当从入门到出师要花很多的功夫和时间。在冲山,许多工匠从小就跟着父辈在樟木堆里长大,小佛手小佛头就是他们的玩具。工棚里面的每个工匠要达到出师独立完成一件作品至少也要花个三年五载。
既要弄懂桌面上大小不一的刻刀、斧子、凿子怎么用好,又要把每尊佛像的容貌和服饰都烂熟于心里,心中才有了佛,才能跟木头对话。一刀一凿子就是佛像的一颦一笑。

雕佛如同修佛。修佛就是从一个无知无觉的混沌状态,通过修行一点一点地放下心中各种的纷扰和执念,最后悟出生命的本真。
做佛雕也是一门减法的学问,一刀一凿地削掉多余的木,从模糊的雏形经过把斜面越雕越细渐显佛相,本来无知无觉的木头在匠人们的琢磨下就变成了充满灵气的佛像。
有人问过一个在冲山的佛雕匠他信不信佛,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天天跟佛在一起,你说信不信?”佛早在不知不觉间刻进了每个冲山人心里。他们这辈子对佛雕手艺的尊重和虔诚在每天的雕刻劳作中,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对佛的信仰和敬畏。


雕佛让冲山人慢慢雕出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只想一心沉下来把整个人交给这门手艺。把一块木最后雕琢成一尊有灵魂的佛像后,匠人在看到成品的那一刹那,仿佛是自己用慈悲感化了众生。
用一辈子时间去表达对一门手艺的尊重,这种坚持比得上任何一种信仰的虔诚。

冲山最多的除了佛像就是船帆。冲山佛雕虽然是门古老的技艺,但在以前是闻名在外,家乡的冲山人大多以捕鱼为生。到了解放后,陈翰彪才把这门手艺带回到了冲山。
因为躲避战乱或者为了生计,冲山的许多佛雕艺人都离开了家乡。陈翰彪12岁就离开了这个小渔村到了苏州学艺谋生。
以前拜师学艺比现在耗的功夫和时间都多得多了。“帮三年、学三年、干三年”,就是头三年给师傅当下人、伺候师傅一家,之后才能真的开始学功夫。

陈翰彪反而很珍视“帮三年”那段日子,因为在雕佛的时候十分讲究心境平和,一旦心有杂念,那一刀下手就会过重,或者线条就会刻歪了,不像画画那样可以把纸撕了重来,一块珍贵的好木材就废了。
19岁就离家的少年,生活的学问、做人的礼仪和做事的态度都在这三年慢慢培养出来。


陈翰彪经常跟徒弟讲一件逸事。在抗日的时候,有一次被日本兵拦下了。看了他带着的刀具立马对他生疑,再看到他手上的老茧,那个日本兵认定他是当兵的,就把他抓回去审问。他希望这些晚辈在平和的年代更加要练出更厚的茧。
虽然已经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但现在许多冲山的年轻工匠在家里学有所成之后,都乐意像爷爷他们那样到外面闯闯。南下福建学习“武派”佛雕的尘世味,更远去到东南亚学习那里佛像的素雅。
只有天地的宽广才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格局。

一个做了佛雕四十年的冲山老工匠说,“尤其是老一辈的,最初选择进这个行当都是为了生计,哪有这么多想法。都是做久了,看多了,才知道这门手艺的讲究。”

这位老工匠当初跟了师傅10年,师傅总觉得他不够火候,不让他出师独立做作品。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师傅,自立门户以后他比以前更勤奋。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会雕了。看着佛头模糊的雏形,心里就是想不出佛的面相。
他厚着脸皮回去请教师傅。师傅看见他很开心。他看见师傅那张慈祥的笑脸后,心里面很清晰地浮现出了一张佛脸。师傅告诉他,一尊佛像好不好,就看你想不想跟祂说话。


现在他的工作台上还一直放着他师傅雕的一尊小佛像。他的师傅前几年走了,现在有什么要请教的就只能对着这尊佛像了。
“佛像的面相和规格只有一个,要让每个人看到你的佛像都会感动,靠的不全是手艺,要靠自己感悟。我现在雕弥勒佛的时候就想着我爸,他很有福相,村里谁都愿意跟他说话。”


匠人在为佛像开相时,心里除了模型,还有那一张张在自己生命中留下过痕迹的众生相。匠人们通过佛像在跟我们对话,他们把对生活的感悟刻进佛像,佛像抚慰芸芸众生。
佛雕是机器难以取代的一门手工艺。机器的速度再快、工艺再怎么精湛,都刻不出谁都想跟祂说话的相。没有人的灵性,造出来的终归还是一堆没有温度的木头。
从佛像微微俯视的眼神和慈祥端庄的微笑会让我们感到,佛对众生的尊重远远超过了众生对祂的尊重。冲山的工匠对待佛像的那种专注和讲究,似乎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对这门手艺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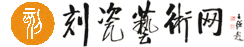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