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四合院坐落在博山区山头镇古窑村的一条东西胡同里,住着他们兄弟三人。大门是用青砖和古窑烧制的窑墼砌成,进门迎面屋山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福字,四个角上各画一只蝙蝠,是“五福临门”之美好寓意。院墙是早年馒头窑烧窑货用的笼盆和垒子匣钵垛成的。北屋住着大姥爷,西屋和耳屋住着三姥爷,东屋住着姥爷,南屋两间大姥爷、姥爷各一间,院子四方且较大,能在院子里骑自行车。
每次去总是先见到三姥爷,因为他不爱说话,好坐在大门口抽烟,长长的烟杆里不知装了多少烦闷,嗞嗞抽烟声里又散发着几多满足与悠闲。三姥姥瘦瘦小小的嗓门却很高,“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的便是她了,想来倒是与沉默寡言的三姥爷很是互补。那时候小,什么也不懂,开心的叫一声“三姥爷”,不等他低低地“嗯”完一声,早已一溜烟跑进了院子。一进院子就能看见大姥爷种的一排排花花草草,不过哪管是什么花和草的熊孩子,看着好看揪了便是。大姥姥长得富态,笑盈盈地出来喂鸡的样子很是慈祥,哪怕我曾经因为在院子里学练骑车,差点撞翻她的鸡笼,也没见她恼过。
还没进屋我就能猜到,我的姥爷准是在屋里看京剧,因为每次只要打开电视,必定是中央十一,一句话唱好久还要转好几个弯,哪有动画片能吸引孩子的注意,没听几句就吆喝着要换台,姥爷也只是笑笑。姥爷只上过两年的夜校扫盲班,却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字,他爱研究周易,给人看日子的本领也算远近闻名,人家要来感谢他,他分文不取,顶多留样水果,好让人心安。姥爷算过我的生辰八字,说我什么都不缺,别人都叫我名字,单单姥爷要叫我“俊儿”,他说叫俊儿长得俊,但我总觉得是因为长得俊才叫“俊儿”。姥爷很少添置新衣服,印象中姥爷的装束总是冬天中山服夏天白色半袖衫,衣领都磨破了,每次却都清清爽爽,熨熨帖帖,再戴上一副老花镜,颇像个老学究。而姥姥却是个闲不住的人,浑身透着一股利索劲儿。一大早爬山拾柴火,一会儿就背回一大捆;或是出门买菜,一买就拖回一小车;我们要吃葱油饼,和面、上烙,眨眼功夫就能把喷香的油饼端到眼前。只要我们去了,姥姥就停不下来地从小屋往外拿东西,一趟拿点桔子苹果,一趟端来饼干点心,一个劲儿地嘱咐着:你们吃啊,多吃点!小时候总觉得那口神秘的小屋里有拿不完的好吃的。
这便是姥爷的四合院,不,是姥爷姥姥们的四合院里的生活。
要说四合院里最热闹的时候,那准是大年初二。我从小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天。一大早起床吃饭,妈妈总说我吃的太少,我撇撇头道,我还要留着肚子去姥姥家吃大餐呢!
赶到姥姥家,小辈们都聚齐了,便一大帮呼呼隆隆地去拜年。纵使就住在一个院子里,也要挨个到大姥爷和三姥爷屋里拜年,说上一句过年好。三家的孩子们在各个屋里串来串去好不热闹!走完一遍,各回各屋,开年大戏才要登场——吃团圆饭。
一桌男席,一桌女席,分别就坐。姥爷讲究,光是凉菜就得六个,切菜要用花刀,核桃仁要用热水泡开剥净,冻粉泡得软硬适中,肉也要提前煸好。每个菜都有配色,一个菜里就有四五种食材,熬麻油、调蒜蓉,切姜末剁得细细均匀,点在菜尖上,如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出凉菜也能如此精致又独特,两桌菜品却又分毫不差,足见姥爷花了多少心思和功夫。早早摆上桌,花花绿绿甚是好看,还没开饭就能让人忍不住偷尝几口。家常小炒不必说,鱼虾海货缺不了,更不用说随便一道菜就耗时颇多的卷尖春卷硬炸肉,藕盒㸆肉豆腐箱。舅舅总会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添个炸鸡柳骨肉相连或南瓜球,放在现在就算小食拼盘了吧,还有最期待的甜饭,甜甜糯糯我的最爱。光吃当然是不行的,还得喝酒。姥爷爱喝点小酒,有儿子女婿们陪着更是来了兴致,喝到兴头上就开始讲以前的故事,我们总得趁着空档跑去给长辈们一一敬酒,无非是说些身体健康之类的话,姥爷也会高兴地多喝上几口。酒喝尽兴,姥姥便张罗着给大家下饺子,吃过饺子,这团圆饭才算吃完。
吃完饭姨和妗子们就开始收拾碗筷。接上好几盆子热水,一人端一盆,一个负责头遍,另一个就负责二遍,再有人就倒水或是沥水放到碗橱里,孩子们争着抢着扫地,抢不着扫帚的就去拿簸箕,一大家子人一起忙碌,连干活都是一种乐趣。
收拾停当,就是饭后娱乐了。大人们凑在一起边打牌边唠家常;我们可对这些不感兴趣,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跟着哥哥去院子里放炮,不过放炮的声音都压不过屋里传来的阵阵笑声。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哥哥胆大,把鞭炮放在纸杯里,嘭得一下就飞起来。我跟弟弟妹妹只敢拿一小盒的摔炮仗,那也能让我们满足地玩到爸妈叫我们该回家了还舍不得走。姥姥会把所有的好吃的分成几等份,一家拎一份,我喜欢吃姥爷㸆的肉干,每次姥姥都会给我多放点。走之前得先跟姥爷道别,他总是简单答应一句便回屋坐着,而我总能从屋外透过窗户看到他追随的目光。姥姥却总把我们一家一家的送到大门口,门口的胡同那么短,姥姥的牵挂却很长,她总会叨念着跟着我们走好久,直到拐弯了看不见了才回去。
曾经我以为,在四合院里的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下去,只是我们都渐渐长大,或工作,或成家,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自打三姥爷去世后,三姥姥一家就搬走了,没过多久,大姥爷一家也搬去了楼房。姥爷的四合院,真的成了姥爷的四合院。
四合院里有了平常没有过的宁静。
姥姥在院里开辟出了一块地,没事种点时令蔬菜,倒也收获颇丰,姥爷没事就拎着板凳去街头晒太阳。他们还养了一只小狗,姥爷疼它,刚下好的水饺都要先捞两个喂它,冬天给它搭窝,夏天给它剃毛。它倒也很通人性,每到傍晚,姥姥去关好大门,就把链子放开,姥姥走到哪,它就跟到哪,讨到些吃的,就心满意足地在院子里撒欢似得跑来跑去,很是欢生。姥姥眼神变得不太好,腿脚也不利索,上不了旱厕,姥爷捡几块废弃的木板,几个袋子,叮叮当当连锯带刨,半天功夫就给姥姥做了个简易却不失舒适的厕所,老年人的浪漫也能甜出蜜来。
可姥姥姥爷还是一天天老去,烧不了地炉,做不动饭菜,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一天,跟妈妈打电话,听她说,姥爷用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套房子,也要搬走了。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却没想过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搬家那天,我没得机会去,可我知道,姥姥姥爷带不走的,有太多东西。带不走姥爷给姥姥做的简易厕所,带不走我充满好奇的神秘小屋,带不走那一方菜地,带不走看家的小狗,更带不走他们一辈子的记忆。四合院里,有姥姥晒过的萝卜干,有舅舅停过的摩托车,有哥哥放鞭炮炸落的炮仗皮,有我跟妹妹跳房子画过的方格子,也有弟弟推着小三轮满院子跑碾过的车辙……可时间的车轮啊,从不曾回头,只向前奔去。
搬去新家,方便又舒服。可姥爷再也不能拎着板凳去街头找他的老伙计,姥姥也不能拉着小车跟我们炫耀自己买的菜新鲜又便宜。在新家里过的第一个年,姥爷自己做不动了,团圆饭却依然没变。一进门,熟悉的凉菜早已上桌;再推开一个卧室门,还有一屋子等待下锅的食材。妈妈说,没到年三十,姥爷就指挥舅舅去置办齐了。弟弟放假,早已陪护了好几天,哥哥带着嫂子从北京赶回来,我抱着刚满半岁的孩子,没怎么出过门,他还有些眼生。终归,我们还是团聚了。
这一年,跟以往不一样。姥姥像个孩子,吃东西会漏又不好意思守着我们带围兜,索性不吃了坐在旁边看,姥爷精神大不如前,却还是硬撑着在自己面前放了一小杯,我都没顾上去看是酒还是饮料,等我们小辈轮番给他敬完了酒,挨个嘱咐一番,才回屋休息。姨和舅舅更加忙碌,而我只能先顾着自己的孩子。没有了串门,不需要接水刷碗,我们也过了抢着吃零食放炮仗的年纪,不变的是姥爷的叮嘱和姥姥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吃饱了吗?再吃点……
在四合院的日子,不再有了。我想念姥爷的四合院,一个院子,把一家人合在一起。可有姥姥姥爷在的地方,就是家,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团圆。
行文至此,我仿佛又回到了姥爷的四合院,这天阳光正好,小狗趴在地上晒太阳,菜地里的菜长势也很好,院子里早已停着舅舅的摩托车,姥姥进进出出忙活着做饭,我刚走到屋门口,就听姥爷说:“俊儿啊,你来啦!”(敬仲二小 郭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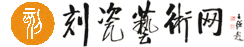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