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始于汉明帝时期,《资治通鉴》记载:“帝梦金人,身高丈六,项佩日轮,光芒四射,金色灿烂,飞行于殿。”明帝遂派蔡愔等人西访,遇迦叶摩腾及竺法兰持佛像、舍利、贝叶经东来。一行人来到洛阳后,明帝赐建白马寺。自此佛教正始传入中原。此后在历代皇帝的推崇下,学佛、礼佛成为时尚,佛教造像艺术也开始兴盛起来。
绘画艺术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佛教利用这种功能寓教义于艺术,把中国绘画当成佛教传播的重要手段。“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绘画艺术的功能被充分利用。“佛像有三十二妙相,八十种好”,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才能,对佛教造像艺术的程式化、类型化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在注重表现人物个性特征、揭示人物心理活动方面,把佛教人物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审美上。佛教艺术的审美思想是佛教思想的形象展示,通过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佛教的“造像图影,颂赞膜拜”成为包括皇公贵族在内的善男信女修功立德的主要活动。佛教的兴盛大力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佛经对西方极乐世界描述是佛教思想的体现,东晋高僧支遁对此这样描述:“西方有国,国名安养,回辽㢠邈,路逾恒沙,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晋言无量寿,国无王制班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各化育于莲花之中,无有胎序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为奇荣,飞沈天于渊薮,寓群兽而率真,闾阖无扇于琼林,玉响天谐于箫管、冥雷陨华以阖境,神风指古而纳新。甘露微化而醴被,蕙风导往而芳流,声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沛清⋯⋯”支遁对极乐世界的描述在敦煌莫高窟220窟得到了充分展现。这组《净土经变》人物众多,楼阁亭台,包罗万象,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幅经变图是艺术家们惨淡经营的结果,构图井然有序,主、次、疏、密、聚、散变化自如,条佛教绘画而卓有成就。
唐代是佛教大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有文献记载的著名画家近四百人,杰出的有阎立本、吴道之、王维、曹霸、张萱、周昉等。吴道子,唐朝著名画家,其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宗教画上,绘制壁画三百余壁,涉及经变、文殊、普贤、佛陀、菩萨及梵天释众等。他的画注重整个画面气氛的统一和具有运动感的表现,给人一种“天衣飞扬,漫笔飞动,下笔有神”的视觉效果。因所绘人物“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后人称为“吴带当风”。其线条自然流畅,奔放不羁,人称“画圣”。苏轼曾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吴道子对佛教绘画的影响主要是一变前代粗细均匀的铁线描,为节奏鲜明、变化丰富的“莼菜条”。“施笔绝纵,皆磊落有逸势”,史称“吴家样”,与南北朝时期的“曹家样”共称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张僧繇、曹仲达、周昉、吴道子、陆探微、尉迟乙僧等或是士族画家,或是宫廷画家,都致力于宗教绘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佛教影响下的中国绘画做出了杰出贡献。
唐朝以后随着佛教意识的渗透,尤其是禅宗思想的出现,许多画家喜欢参禅论道,佛画多为寺风景、道释人物,讲究意境、气韵与趣味。唐代王维宋代苏轼为代表的画家以禅入诗、以禅入画,直接影响了中国绘画风格的转变,出现了一大批尚意风格的画家。五代以后,绘画内容也从画佛像传播佛教思想的绘画形式,逐渐发展为禅僧与文人士大夫直接表达“顿悟”思想的一种绘画形式,“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以山水、人物,花鸟为表现内容的禅宗写意画逐渐兴盛起来。
贯休,五代时期著名僧人画家,工草书时人比之怀素,“画罗汉十六尊帧,厐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梵相胡貌,曲尽其态”,又画释迦十弟子亦是此貌。罗汉画继承唐西域画家尉迟乙僧画风,并借鉴唐阎立本的线条遒劲、气势磅礴的笔法,画中罗汉庞目大耳、曲尽真态。
宋代李公麟,在佛教绘画上首创“白描式”佛像,画风“出奇立异使世俗惊叹”。这种白描不施色彩,纯用墨线勾勒,表现力生动形象,扫去粉黛,轻描淡墨,意与禅会,超凡脱俗,成为集顾、陆、张、吴画法的集大成者。自此以后那种庄严精彩的供养功德画逐渐式微,自由挥洒的文人写意画逐渐风行。李公麟的画敢于突破陈规,所作《长带观音》《石上卧观理清晰,节奏分明,创造出“远岫与云容交接,遥天共水色交光”的辽阔境界,做到了“咫尺之图,写千里之境”。正是佛教这种美轮美奂的境界,给中国绘画艺术以无尽的启迪,使艺术家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用高超的艺术手段把宗教的审美情趣充分发挥出来。
佛教理念既有天堂也有地狱,世间万物都在六道中轮回,行善者去极乐世界,作恶者下十八层地狱。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曾画《地狱变相》,画中鬼神“髯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而整幅图画“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化阴惨,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其效果竟能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足以说明佛教思想在吴道子的形象描绘下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充分发挥了艺术的教化功能。佛教的传播丰富了中国绘画的题材,拓宽了绘画的视野,《净土经变》《无量寿经变》等经变画的出现给中国绘画在宏大场面的布局构思、人物群像的塑造提供了灵感。人物类型诸如佛像、菩萨、罗汉、明王、高僧、天龙八部等直接催生了中国绘画的一个种类——释道人物画。

[南宋]金大受 十六罗汉图轴 172cm×77cm 绢本设色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纵观中国历史,佛教越兴盛绘画艺术就越发达。盛唐的莫高窟壁画,北魏的石刻造像,都是因为统治者笃信佛教、崇尚佛教,才使得佛教有了长足的发展,绘画艺术也跟着兴盛起来。在佛教思想意识的影响下,中国绘画的审美理想就建立在冥会、止观的境界上,这种崇高的精神状态让人们在虔诚的修行中得到证悟和解脱。这与绘画艺术的畅神功能不谋而合,寓教于艺,艺教互融,使中国绘画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美学体系,为中国画的审美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印度佛教绘画在技法上给中国绘画也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图案丰富多彩,构图纷繁复杂,色彩瑰丽多变,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语言。汉魏时期传统纹饰主要以龙纹、云纹、卷草纹为主,佛教传入后,纹饰图案千姿百态。有藻井的莲花、伞盖,有桁条上忍冬、云气、火焰,有彩绘垂幔以及悬挂的兽面、玉佩、流苏、羽藻。边饰则有莲荷纹、星象纹、鸟兽纹、棋格纹等。后期又发展了多样纹饰,葡萄纹、石榴纹、茶花纹、宝相花纹、游龙戏凤纹、化生飞天纹以及凌锦花纹。这些花纹装饰时而生动活泼、爽朗明快,时而庄重严整、浓艳富丽,大大提高了中心画面的表现力。
汉魏之前,中国绘画主要是平面构图法,以排列对称为主。印度佛教绘画传入时使用的是晕染法,东晋画家张僧繇在南京一乘寺用此法作画:“一乘寺梁邵陵王伦所造,寺门遍书凹凸花,其花乃天竺遗法,用朱砂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咸平,乃名凹凸寺。”张僧繇所画这种花就是用深浅渲染法分出明暗阴影,这一绘画技法的出现在处理透视与色调的对比上对中国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僧繇用此法作画被称为“张家样”。
佛教绘画在色彩运用上对中国绘画开创了一条新路。佛教绘画用色大胆,色彩浓重醇厚,光耀炫目,富丽堂皇。所用颜料品种丰富,有石青、石绿、朱砂、银朱、朱磦、赭石、土红、石黄、藤黄、靛青、蛤粉、白土金箔等数十种之多。唐代画家周昉师承张萱,用色华丽典雅,超凡脱俗,从其传世作品《虢国夫人游春图》《游春仕女图》看出其善于用色彩表现人物个性特点,史称“周家样”。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梁武帝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大肆造寺度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当时的写照。这时期的著名画家张僧繇把中国书法中的点、曳、斫、拂与佛教人物创作相结合,创出“张家样”。唐代李嗣真这样评价张僧繇:“顾陆已往,郁为冠冕,盛称后叶,独有僧繇。今之学者,望其尘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顾陆人物衣冠,信称绝作,未赌其余,至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千变万化,诡状殊形,经诸目,运诸掌,得之心,应之手,意者天降圣人,为后生则,何以制作之妙,拟于阴阳者乎。”
《历代名画记》记载:“连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肩背,亡遗尺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曹不兴即东晋曹仲达,他长于佛教绘画“按西国佛画仪范写之”,人称“曹衣出水”,史称“曹家样”。随后的卫协、顾恺之等在绘画造型上无不师法印度佛教绘画而卓有成就。
宋初画家石恪,滑稽善辩,博宗儒学,画佛道人物“笔墨纵逸,不专规矩”,人物手足用细笔画法,衣纹乃粗笔成之,所作《二祖调心图》,慧可双足交叉跏趺坐,以胳膊支肘托腮作思维状,另一幅伏于温驯如猫的虎背上,以虎为枕,现出高僧修行深厚、法力无边。图中高僧的头脸用淡墨勾出,身躯衣纹则以狂草笔法,再以淡墨渲染,开大写意人物画之先河。
梁楷继石恪后,承继石恪大写意的画法,又有所创新。《六祖斫竹》是梁楷晚年作品,旨在表现六祖慧能,“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一改线条的劲细绵长,笔墨简洁率意,“心之溢荡,恍惚放佛,出入无间”。画面简洁酣畅,用笔粗起细落、变化多端。这种不拘于形的艺术风格,契合了南宋明心见性的禅风,对清初八大山人的画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代佛教绘画艺术成就稍逊于前代,赵孟頫是佛画的代表人物。他的《红衣罗汉图》风格浑穆,图中罗汉着朱红袈裟,盘膝侧坐左掌平伸,神志安详坚毅,生动典雅,古意盎然。赵孟頫提倡“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红衣罗汉图》是其主张的具体体现。元代另一位画家颜辉,擅长道释人物,师法梁楷、法常,笔法粗厚,勾勒粗细成宜,起伏有致,渲染精到,以水墨烘晕,使画面衬托出阴暗凹凸,富有立体感。颜辉的代表作《水月观音》,图中观音丰腴秀美,双目微闭作沉思状,双手抱右膝半跏趺坐,身旁静瓶中插柳枝,身后绘一轮明月,山涧飞流,翻滚而去,真乃“笔法奇绝,八面生意”。
明代寺观壁画的盛行涌现出了张仙童、蒋子游、张靖、上官伯达、丁云鹏、吴彬等一批佛派画家,其中丁云鹏得吴道子法,白描学李公麟,设色学钱选,其佛像人物画以精细见长,丝发之间而眉目意态毕现,“画大士罗汉功力精深,神采焕发,展时间恍觉深入维摩室中,与诸佛对语,眉睫鼻孔皆动”。
清代善画道释人物的丁观鹏,画风工整细致,受西方绘画的影响颇深,其《法界源流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描金设色,精致瑰丽,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
清代另一位画家金农,“涉笔即古,脱尽画家时习”,《佛像图轴》画释迦牟尼佛,神情肃穆,身披袈裟,袒右臂,拱手肃立,面部和手臂施彩,衣纹粗放,加上画面空白处全部题写诗文,与传统清逸画风形成鲜明对比。
清初“四僧”,虽不直接画佛像,但其山水花鸟开一代新风,成绩斐然。弘仁之秀逸,八大之冷峻,髡残之简练,石涛之苍润,无不体现了寓“禅”于画,禅意与画境相生的绘画理念。
佛教除了在审美、技法、题材等方面对中国绘画产生巨大影响外,还对绘画理论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谢赫的“六法”、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苏轼的“传神论”、刘道醇“六要六长”、郭若虚的“三病十二忌”、石涛的“一画论”等,都是受到了佛教理念的启发总结出来的理论。
总之,佛教是绘画发展的源头之一,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了全面影响,可以说没有佛教,就没有中国绘画的辉煌成就。中国绘画也使得佛教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因相生心,心佛一体”,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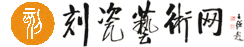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