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为形役,尘世马牛;身被名牵,樊笼鸡鹜。
——陆绍珩《醉古堂剑扫》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本色的人生也是如此。

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枯竭,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

“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最完美的生活都是本色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

本色人格兼具了严肃与豁达。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既已碎,顾之何益?”
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堕甑不顾、雪夜访戴看起来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
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俗语说的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无本色,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枯竭。“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
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

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命上的“苟且者”,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大半都是剥离的生命本色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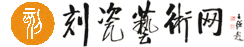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