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朱一圭1952年开始研究乌金黑陶立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成功研制出高温花釉,博山陶花釉在全国始终居于领先位置。五十年过去了,朱一圭先生开创出的高温花釉艺术,在传承人朱润生、薛艳君手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标志着中国北方高温花釉艺术登上一个新的高度。
11月7日,当我走进朱一圭先生的陶瓷艺术研究所,看见一件件硕大的花釉瓷器,不禁喜从中来,这一百件“圆满系列”花斑玛瑙釉大瓶,由朱一圭先生创意策划,在润生、艳君手上成型,完成了博山艺术陶瓷由陶花釉向瓷花釉的完美过度,这是中国陶瓷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
博山花釉源自宋代博山窑。多处博山古代窑址都出土过白瓷、乌金釉、三彩瓷残片。但细心的朱一圭先生从更小更残缺的瓷片上发现了玛瑙釉。他笃定决心要一一复原这些历史名釉。后来,这些课题在朱一圭先生这里都得到实现,以致1979年邓小平带着朱一圭创作的20吋《竹鸡挂盘》成功访美,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信念。但是,直到最近三年,朱一圭高温花釉艺术仍然属于陶上花釉阶段,虽然这种画面具有古旧醇厚的韵味,但烧成温度低,色彩还原不彻底,在一些更靓眼的陶瓷装饰艺术面前,还是朴拙感有余而现代感不足。而瓷上花釉,无疑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
瓷花釉,在淄博陶瓷发展中曾经展露过一次端倪。六十年代,淄博硅酸盐研究所总工程师、知名陶瓷材料研究专家刘凯民先生,曾以均瓷残片为对象,分析色釉成分和形成机制,在实验室研究成功兔毫、蓝钧瓷上花釉样本。由于历史局限,国家更多财力人力都压在日用陶瓷研究开发上,瓷花釉永远止步在实验室阶段。半个世纪过去,如今,臻于成熟的瓷花釉终于在博山新生代陶瓷艺术家手上诞生出来,朱一圭先生把这个新釉种命名为花斑玛瑙釉。
从屋漏痕、蜡泪堆,到禅意表达
朱一圭对传承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朱一圭陶瓷艺术生涯,历来倡导动手,以手眼的勤奋恪守工艺路线。传统花釉艺术,施釉的时候动一大番脑筋,预设出某种程式的效果,烧成以后发现并没有出现,而有时候基于某种条件,一开窑门,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无可复制,带给人的喜悦是不可言说的。到了晚年,朱一圭开始琢磨怎么样叫花釉再上一个层次,再来一个突破,怎么达到宋代博山陶瓷的最高水平,当高温花釉真正达到了一个巅峰,还能往哪里走?
观察朱一圭先生的高温花釉作品,大多以高温条件下釉料自上而下的适度流动为主要美学追求,类似屋漏痕、蜡泪堆,后来朱一圭先生开始重视釉面的自然变化。开始是在盘上,通过人工一层一层施釉,在平面上找到一种变化,让变化更丰富。后来是在器皿上寻求自然的变化,淡化人工,开始做减法,更多让材料说话,让窑炉说话,让火焰说话,在弧形纹理和线条的运动中追求禅的意境,把自然的成分进一步扩大,自然变化的禅意的东西越来越居于显著位置,主导一件作品的审美价值。润生开始并不理解,觉得还是尽量钻研工艺流程,追求流程的复杂和完善,得到的作品才会尽如人意。后来,随着年龄增长,阅历的丰富,发现许多东西真的可以简化,而且必须简化。艳君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由原先的手眼在先到最后形成四分人意六分天工,通过窑炉和火焰,让它去自然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效果,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人与自然在花釉上结合是最生动最典型的。
一个陶瓷艺术的重大嬗变将要在这个陶瓷艺术家族发生。
审美突破,倒逼花斑玛瑙釉铿然出世
每一个出窑的早晨,一窑的东西都摆在那里,朱一圭召集大家开始点评,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讲述,一讲就讲一个晌午,这些不断絮叨重复的东西,似乎在一朝之间成为润生、艳君这代人的不二法宝。朱一圭的理念在润生、艳君身上慢慢得到了消化,年复一年的说道,他们只是听着,攒着,到了某个年纪,经历了某些事情,倏忽开窍,父辈的想法和思路何其正确。遗憾的是朱一圭先生坐拥无限的艺术资源,偏偏不去做自我推介,干就是了,这个非常朴素的思想唯一的初心是,把泥土烧成陶瓷,换钱糊口容易,那不是陶瓷艺术存在的意义。
前后两代人,在陶瓷艺术的核心价值上找到了契合点。还是在高温花釉上寻找突破。从陶花油到瓷花釉,经过了一个不长的过程,艳君在一些小型器物上实验,基本都能成功,始终未能在大型器物上应用。但在手拉坯大型器物上开拓,还是润生的大胆决断。
朱一圭先生逐渐放手让下一代传承接班。润生告诉艳君,你就大胆弄吧!烧烂了就烧烂了,不要有任何顾忌。十几岁就从事施釉立粉的薛艳君沿着朱一圭毕生积累的独门秘诀,进行了不同的尝试,浪费也只多不少,每每小有成功,觉得十分精彩,大大出乎预料,这极大唤起了他们突破的兴趣。问题也跟着来了,想获得彩釉画面的奇异效果,必须增强釉料的流动性,增强釉料的流动性就得提高烧成温度,提高烧成温度受到当地陶土的局限和制约,不是出气泡就是出结晶,而回到过去的烧成温度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瑰丽画面的。润生说,换材料,用南方瓷土混合当地材料,一定要把温度烧上去。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
烧制方法与原先没有任何区别,升温曲线也一致,但严格规定了烧成时间,依据工艺和材质的变化,烧成时间有所延长,不能低于9个小时,比常规烧成时间超长两三个小时。温度也大幅提高,花釉多而厚,没有一定时间熔化不开,固体不流动,或流动不完全、不精准,效果就出不来。烧成温度提高,再提高,最后达到了充分瓷化的1300℃。景德镇瓷泥为主体,密度更大,瓷性更强,白度更高,增强了坯体材料的稳定性。瓷土吃温高,亮色程度大幅提高。釉色仍然沿用当地釉色,在新坯体上更容易表现釉色的饱和性、丰富性、过渡性,釉面光亮、平滑,器物完全成瓷。他们集中精力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百件花斑玛瑙釉精品,几乎融入了全部高温花釉的技巧,也得到了所有高温花釉的表现效果。这是一百件大型手拉坯高温花釉,以圆柱形和圆形罐为基本外型,器型硕大,釉色极其丰富。这一百件作品,已经完全脱离传统陶系花釉,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百件圆柱形和圆形罐,正是朱一圭先生在几年前摹画过的“圆满系列”。
“三一”铁律升级版,让瓷花釉大美倾城
瓷花釉成功了。回想过往,朱一圭先生时常在嘴上念叨的东西一一再现。长年沉浸在陶瓷艺术氛围,一个人被浸染是毫无觉察的。小猫小狗老虎老鹰,喷上点颜色烧出来也挺好,但不足以表达高温花釉的神韵,也就失去了高温花釉的意义。朱一圭先生是坚定的陶瓷艺术论者,不追求量,这也形成了独有的经营模式,至今仍然如此,从来不按计件组织生产,一件作品做一天也行三天也行,多咱做好多咱算数,以产品和作品说话,不走流水线作业。如今,朱一圭先生的这些观点被润生他们准确理解和接受,觉得老父亲确实超前。
花斑玛瑙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色彩肌理丰富,更加追求自然变化,人工的部分更淡化但更专业,自然的东西超过了一半,通过对火焰的控制让画面出现预想或想象不到的效果,表现更丰富更现代更抽象更写意。用色因而更加大胆,彻底放开,不为窠臼所囿。以前不敢用的颜色开始没有顾虑地使用。将三个色彩扩张到三大色系,没想到越大的器型,颜色越纯,亮度越显,层次越丰富,越具有超乎想象的表现力。越大胆,效果越惊人,这是过去使用当地陶泥料所做不到的。十几种颜色在一件作品上叠加,红,不再是单一的红,而是复合的过渡的多层次的红,其它颜色也是这样,极大丰富和拓展了花釉的表现力。过去他们不敢,朱一圭先生曾经给他们制定过一个“三一”铁律,一件器物上只能使用三种单一颜色,不能出现第四种,在三种颜色的转换中寻找好的呈现。现在,创新的大门洞开,是三个色系在一块共同表达,只要是一个色系、一个色调,不分冷暖强弱,都可以大胆使用。看上去一个主色调背后有无数种颜色托着它、支撑着它,丰富性超过任何以往,又没有花哨和混乱的感觉,原因就是没有跑出三个色系的控制。规矩中更多变化,变化中不逾规矩,看上去还更加舒服。上红色,上去就是五六种,深浅过度不一。蓝,又是三四个蓝,深蓝中蓝浅蓝,搭配起来。既没有脱离朱一圭先生立下的“三一”规条,又大幅提高了其艺术表现力。
依我的判断,这一百件花斑玛瑙釉大瓶放在中国美术馆、上海朵云轩,不会给博山人丢份,也不会给北方艺术陶瓷丢脸。
一场立冬大雪将要来临。匆匆与润生告别,他送给我一件“三才”瓷花釉盖碗存念,天、地、人各适其位。可沏茶品茗,可赏心悦目,我却以为大有深意。“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系辞下》)“三才之道”到底还是会通之道、和合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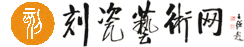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