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常素芳总在一旁注视着张明文刻瓷
张明文在刻瓷,多年刻瓷让他双眼习惯性眯成一条线。
张明文的作品墨梅刻瓷盘,此作似在宣纸上作画,画面苍劲
湘云醉卧刻瓷瓶,用钻刻法行之,湘云在花丛中熟睡、芍药花飞满全身的情境跃然瓶上
《纪泰山铭》白瓷鹿头尊。铭文内容随形而向,用钻刻法刻出隶书结构,平头楞角突出金石趣味,使整个作品浑然一体。
惊鸿一瞥半生缘
走进张明文的家,映入眼帘净是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瓷瓶。不要小瞧这些物件儿,这可不是普通的器皿。你看那上面,错落的山水、苍劲的书法、传神的人物,或细微、或粗犷、或工笔、或写意,古朴典雅藏而不露,既有浓郁的金石趣味,又有笔墨淋漓的水墨妙趣,令人惊叹。这些都是张明文的刻瓷作品。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也许这句古话说的便是刻瓷吧。刻瓷,是我国传统的陶瓷装饰手工艺术,艺人在白瓷器上用墨写字或绘画,然后,用特制的刀具依据墨稿雕刻出来。它有笔锋描抹不可代替的独特韵味,被视为特种手工艺品,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刻瓷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融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集笔、墨、色、刀于一体。张明文工作的前十几年,绘画、雕塑、书法样样都做,而立之年才接触到刻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鸣天下闻。
张明文1941年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乡一个农民家庭,17岁那年,张明文走进淄博瓷厂的大门,成了一个工人。
张明文说,“进厂以后粉碎、成型、施釉、烧成这些工种都干,大部分是体力活,很艰苦,但是也搞明白了陶瓷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工作虽然辛苦,但张明文却不以为苦,因为他有自己的乐子———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有空我就在废信封、废牛皮纸上画人物啊,画花鸟啊,画一画,就不觉得累了。”
张明文把厚厚一摞子画都压在了铺床的草席子下,有一次同宿舍的工友无意中掀开了他的草席,看到了这些画,很是惊讶,拿了一些去给厂长看。
“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我,不要在这儿干了,你可以去彩绘组了。”张明文被调到了彩绘组。由于表现出色,厂里又送他到外地进修学习。这些学习机会让张明文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知识和技艺,他如饥似渴地学,如痴如迷地钻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张明文与刻瓷艺术结缘,始于1970年。那一年,淄博瓷厂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电子工业产品展,张明文作为驻展美工被派到北京。他怎能放过这个学习的好机会,趁着休息时间一个人跑去故宫博物馆参观。
“在陶瓷馆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一块瓷板,格外特别,它与普通瓷器的画工都不相同。虽然隔着玻璃看不清楚,但那种朦胧的美却更令人感到奇特和神往。我请教了一位参观的老者,他告诉我,这是清代末年著名刻瓷艺术家朱友麟的作品《采菊东篱下》。”
“哦?刻瓷?怎么刻?”这是张明文第一次听说刻瓷,脑子里有很多个问号。他回到淄博后,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疑问,但这块美丽而神秘的瓷板却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挥之不去。
又是四年过去,1974年,张明文认识了来自青岛的艺术家郑惠民。“他拿来了一个小瓶,上面有一朵牵牛花,画面既像是国画,又有金石味道,我一看就认出来了,这是刻瓷!”
回忆与刻瓷四年后的“重逢”,他激动依旧:“那个瓶子这里一片叶子,旁边还有一片叶子、几条枝蔓,上面一朵花。”他拿起手边的一个小白瓷瓶,边说边拿起毛笔、蘸上墨汁画起来,几笔就勾勒出来了,“印象太深刻了,忘不了。”
那一天的饭桌成了张明文的课桌,他刨根问底请教刻瓷的技法。“回到家我马上找来刀、锤、瓷瓶,垫上抹桌布,让爱人扶着,叮叮当当描刻起来。”事实上,刻瓷,前人所留经验甚少。“清康熙年间,虽有艺人高手用钻刀在瓷面上刻画图案,但终因其有相当的难度,而没有留下文字技法资料,因而刻瓷传世珍品更屈指可数。”张明文遗憾地说。
瓷器的釉面光滑且脆,而用钻刀刻画,无疑是以硬碰硬,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爆裂,一件即将成功的作品会前功尽弃。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中,以刻瓷的难度最高,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谈起那段日子,张明文的爱人常素芳记忆犹新:“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不停地敲打、观察、琢磨,也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他有股子犟劲,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常常干到很晚,很少按时回家吃饭,我常常和孩子们吃了晚饭再去厂里找他。那时候,厂里晚上固定时间锁门,他被锁在车间里是家常便饭,我还和他一起爬过好几次大门呢!”
那时,一家5口人住14平方米的平房。为了给张明文的创作提供空间,每周日常素芳都带着孩子回娘家,张明文则把褥子掀起来,以床为工作台,在床上练活。“夏天没有风扇,那时候真是挥汗如雨啊。”张明文感慨道。
求索之中,张明文第一件成功的刻瓷作品诞生了。
这件作品被当时的厂长槐兴亮看中,把它放到工厂的展室里,正巧被来瓷厂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从此,淄博刻瓷名声大振。张明文艺术生涯的轨迹就此改写。他拿起的刻刀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随心挥刀锦绣出
看张明文刻瓷真是一种享受。但见他左手捏住刀具,右手握住小锤,双眼微眯聚焦着瓷器,两只手像弹琵琶那样敏捷,錾头随着轻声的捶击,雨点般地落在洁白如玉的瓷盘上。上墨前分辨不出他所刻何图,惟听刀响咝咝,锤声叮叮,待到敷色上彩,人物、山水、花鸟才跃然盘上、呼之欲出。
刻瓷,工艺并不复杂:第一步在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第二步依据墨稿用钻刀刻画、凿镌,第三步填色即可。这三步,在刻瓷艺人眼中,缺一不可。
可是,张明文却有了新想法。“照稿刻凿的确失误很少,但是我却常常觉得墨稿会限制我的想像力,让我的作品僵硬呆板,缺乏摄人魂魄的灵动感,能不能摆脱画稿,以刀代笔,直接錾刻呢?”
刻瓷,不像作画可以涂改,一刀下去即成定局,稍有不慎,前功尽弃。为了实现脱稿刻瓷,张明文开始孜孜不倦地练习把画稿烂记于心,凭忆而刻。
宝剑锋从磨砺出,张明文终于练就腹藏千稿、挥刀成画的本事,刀刀见笔意,处处有风骨,无稿而刻的本领很快让他在刻瓷界中崭露头角。1980年,机遇再次降临,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人员现场考核选拔,张明文被派往国外进行刻瓷表演。
“刻瓷还能出国表演?想都没想过啊!但很快就激动不起来了,得准备作品啊。”
1982年,张明文被派往美国田纳西州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博览会,在美国一呆就是8个月。关于张明文在美国表演刻瓷的情景,有美国当地报纸这样写道:观众层层叠叠,个个跷足引颈,凝神静视着一个面颊清瘦、两鬓挂霜的中年人的一举一动。只见他在一个洁白如玉的瓷盘上,以娴熟的动作,时而举刀扬锤,时而调色赋彩,随着画面的出现,人们不断发出赞叹,并频频询问译员,“他的画稿在哪里?”“他像一个很好的脑科医生!”……
张明文娴熟高超的技艺让世界人大开眼界,美国前总统卡特看了他的表演后,称赞他是“真正的艺术家”,美国媒体盛赞他“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艺,像脑科医生的手术刀那样准确无误”。由他刻制的420多件作品被抢购一空。博览会结束时,张明文为国家创外汇49900美元,这在当年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8个月后,张明文载誉而归。爱人常素芳一见他,眼睛就湿润了:张明文脸色苍白,两鬓添霜,好像大病初愈一般。“人家出国回来,满面红光,你咋瘦塌了架?”张明文笑笑说:“你当出国是去享福?每天都从早上十点开馆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闭馆。不过一想到祖国,拼劲就上来了。”
万般技法尽上瓷
“我从事刻瓷30多年,很是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建树,但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那就是为了传承老祖宗这门艺术并发扬光大,我一直没有放弃创新。”张明文谦虚地说。
刻瓷艺术虽历史悠久,但它使用的器具一直十分单一,艺人们大都使用天然钻石和硬制木材做雕具。为了突破传统器具对雕瓷工艺的局限和制约,张明文在实践中大胆创造了两种刻瓷工具。
“一个是钻石扁形刀,一个是丁字形刀。有了这两个工具,对线条的把握就能更准确,刻起瓷来,也更得心应手。”
工具好用了,他就琢磨一些新的刻瓷技法。
“传统技法有钻刀法、双勾法和刮刀法。”张明文介绍说,钻刀法是用小锤均匀地敲打钢钻刀,使之在瓷器表面形成大小、疏密、深浅不同的点,构成画面或字体。双勾法是用锐利的金刚石刀沿字体或画面的外轮廓刻画。刮刀法是先用双勾法刻出字画轮廓,然后再将双线间的瓷釉刮去,以便填色。
“刻瓷十分讲究刀法,要既能体现传统书画艺术风格,又能保持瓷器表面的晶莹光洁,形成独特的效果。为了让刻瓷作品能有更丰富的表现力,我真是没少花精力琢磨新技法。”
为了增强刻瓷作品大写意画水墨淋漓的效果,张明文从宣纸水墨画中受到启发,他先用湿布擦盘,趁水迹未干作画,然后用细刀刻出水脉,淋漓洇润之趣跃然盘上,被称为“水墨刻法”。为使画面更加丰富持重,张明文先用双勾法刻出人物衣纹线条,然后用钻刻沿线条刻出密集的不规则的冰纹,纹路由聚到散,画面更有层次,连衣饰的质地感、名贵感都被生动地表现出来。这种独特的敷彩方法所达到的效果,是绘画所不能企及的,他命名为“钻刻冰纹敷色法”。
刻瓷艺术在张明文的刻刀回转之间不断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刻瓷的工具、刀法、着色等进行了大量改进,还将高超的陶瓷制作技术和娴熟的书法绘画艺术一起灵活运用于刻瓷之中,使刻瓷作品集国画、版画、油画、素描之长,逐渐走向完善。
“我老伴不喜欢和我一起出门,她总说我出门的时候不专心,看到什么好东西就往刻瓷上琢磨。”张明文说。
这话不假,他的许多刻瓷技法就是从平日的游玩中获得灵感的。“泰山顶上两块碑,汉武帝立下的《无字碑》和唐玄宗撰书的《纪泰山铭》碑,一简一繁,对比鲜明,却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分量。我就想啊,能不能在一件器皿上同时显现这两种风格呢?即有丰富的内涵却又不失简约之美。”
张明文由此创出了瓷面微刻法。1991年,他把《论语》的2万多字刻在一套五头文具上,远看一字没有,近看则字字清晰、满目琳琅,耐人寻味。
这“微”,有多“微”?比一比,三个小字才一个米粒那么大。陶瓷面滑坚脆,运刀吃力,易于崩缺,字距行距须得一气呵成,若非技艺精湛、气定神闲之人不敢涉及。张明文为了刻这套作品,竟是换了几把花镜,从150度升到了400度,断断续续刻了一个多月,刻得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就这么眯着眼一直刻,后来实在看不清了,被拉去医院检查,并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这套作品获得了首届“全国轻工业博览会”金奖。
2002年,61岁的张明文又将刻瓷艺术运用到薄胎瓷上,发明了薄胎瓷刻瓷艺术。他独出心裁,制作了专门的刀具,在一高36.8厘米、壁厚不足1毫米的薄胎瓷瓶上刻作了一幅“史湘云醉卧芍药茵”,红楼梦人物优美各异的形态生动逼真。
“那滋味,真是如履薄冰啊。普通瓷器差不多3毫米厚,这个薄胎不到1毫米。刻的时候啊,胆颤心惊,恐怕这一刀不用力呢,就刻不出痕迹来,稍一用力就刻破了。”就这样,刻破了三个大瓶之后,张明文终于成功了,而他从此也开创了在薄胎瓷器上刻瓷的先河。
张明文总说,法无定式,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的艺术氛围中不断实践而总结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他深入民间,向民间刻瓷艺人虚心学习,与他们深入探讨刻瓷在艺术上的可建构性,在这期间发表了多篇对刻瓷工艺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
“刻瓷不应该只有实践经验,还应该从理论上指导实践,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刻瓷艺术与情理法趣》,对刻瓷的渊源,刻瓷与绘画、篆刻、书法的关系及刀法、着色的运用等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张明文还编写了《刻瓷教学大纲》,在全国推广刻瓷技法和刻瓷工艺。
不求名利求传承
有人说,张明文是个怪人。2007年1月他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从北京领奖回家后,所有庆功会、表彰会、请客吃饭都不参加。“老伴、女儿、女婿都劝我去,可让我喝酒、应酬,我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老头子不愿干这个。”
张明文虽然做人低调,但只要涉及到刻瓷艺术的发扬光大,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冲在最前面。山东省在刻瓷方面有51个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或者陶瓷大师,至少40个直接或者间接受过他的指导。“刻瓷成了很多下岗职工养活自己的饭碗,也让很多人有了赚钱的本事,目前淄博市大约有8000人专职或者业余做刻瓷,尽管良莠不齐,但是我很高兴,很欣慰,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作为淄博刻瓷的领头羊,张明文觉得自己不辱使命。
大多数时候,张明文给我的感觉是位严谨而儒雅的长者,但一谈到刻瓷,他马上就神采飞扬。
“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只有文盲没有美盲,他可能不识字,但是对于艺术作品啊,不管他的欣赏水平多高,他都懂。所以刻瓷要用心,用情感,这份情感和心意会随着瓷器传递给别人。”张明文总是这么说。
张明文讲了一个故事:“一次有人请我刻一个瓷盘,他们要送给一个泰国华侨。我想了很久,给他刻了一幅山水,还在上面刻了一首我自己做的小诗:清清漓江水,朗朗笑语声,人在画廊里,山川自在胸。当这个盘子送到那位华侨手中时,他当场流泪了,后来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说这个盘子上的山水和小诗勾起了他无限的思乡之情。”
天马行空的构图,偏偏又充满力量,因为倾注了情感,瓷器便有了感人的力量。
“凡是能传承的东西,必然是文化产品。其他东西都吃了、喝了、用了,也就没有了,惟独有文化、有内涵的工艺美术产品能一直流传下去。我要做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商品,而是要能一直传下去的艺术品!”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他当作宝贝的、想要“一直传下去的艺术品”,大部分并不是安放在百宝架或者保险柜里,而是塞在他卧室的衣柜顶上。张明文的卧室很简单,一张大床,对面两个大衣柜,衣柜上面整整齐齐地塞着好几个装瓷器的盒子,每个盒子上面还贴着纸条,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写明盒子里面装的是哪件瓷器。“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柜顶上的这些盒子,心里就踏实。”
每每谈到他的一件件得意作品,张明文就脱了鞋、爬上床,踮着脚、伸着脖子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拿下来,不要别人帮忙,自己像捧着个婴儿般的谨慎,看完了再小心翼翼放上去,不厌其烦。
“我的每件作品都是投入感情来完成的,我都很爱,虽然也发生过有人找我讨了作品又拿去拍卖的事情,但过去我从不卖作品。不过,从去年开始我也尝试卖作品了。”
“为什么要打破自己的原则?”我问。
“独木不成林。要想让刻瓷发扬光大,单靠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其实社会上有些人想认认真真把刻瓷当事业但没有工作场所,对刻瓷心怀抱负却得不到承认和重视。我准备申请成立一个刻瓷艺术研究所,广纳有绝技、有创意、有恒心、能忍受寂寞甘坐冷板凳的人,给他们工资高高的,让他们不愁吃穿、有空间来钻研。这就像弹钢琴一样,把不同人的风格、技巧、绘画、创意等等组合起来,每个音符发出不同的声音,却奏出动听的曲子。”
有人算了一笔账,张明文为瓷厂创收的外汇够给他发180年的工资了。如今,他早已退休多年,每月拿着刚刚增加到1400元的退休金。张明文对此很觉坦然。
在张明文的家中,我读到一首他自己写的小诗,其中一句很有味道:“冬季那冰清玉洁的花朵,是因为经历过冷遇,甘于寂寞只是为来年的壮丽。”
“甘于寂寞”我可以理解,否则您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你自己可曾经历过冷遇?”我问他。
张明文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我,他转头望向窗外,读了一句诗:“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眼中闪着坚定的目光。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张明文用他40年陶瓷人生的执著追求诠释了这句话。每每想起与张明文的第一次见面,心中仍澎湃不已。回想第一眼见到张明文时的情与景,苍茫一色的天地恰如一个洁白无瑕的大瓷盘,而着一身皂衣的张明文恰如瓷盘上的刻画,那么坚定、清晰而有力量,一雕一琢处,尽见风骨;精錾细刻间,总有乾坤。(文章源自经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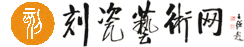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