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走的太突然了,令人难以接受!
初六我到保定的他的住处去看他,在那呆了三个多小时,陪他聊天,给他说笑话,尽量逗他开心。然后又陪他到院里去散步,走一会,坐一会,在院里的小广场上,有健身器材,还作了一些简单的运动。坐下来休息,我看着他吃了一个烧饼,他执意要我吃一块,这样我掰了四分之一,他吃了四分之三,完了又喝几口水。我开玩笑说,你这能吃能喝的,有什么病呀!因为家里人说,他中午就没吃几口饭。我说人是铁,饭是钢,只要你能吃饭没事的。没想到事隔一天,竞突然走了。
感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料!
有多少心中牵挂的,放心不下的,一瞬间便都撒手了。。。。。。
今天是大师走后的第三天。这个夜晚仍无睡意,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眼前浮动的依然是大师鲜活的形象。
依然是那个下午,阳光暖暖的照进窗户。我们在客厅里面对面聊天。陈大师坐在椅子上,腰板挺直。下身穿黑色长裤,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衫,精神很好。说了一会,我怕他累,就说要不要回卧室休息一会,他说行。于是我扶他到卧室,扶他侧身躺下。这段时间他因为心脏不好,已不能平躺,也因为右臂无力而不能自己轻松地躺下和起来,每次都需人来扶持。我拿个小凳坐在床边,顺手为他按摩左手臂,他说你也歇会吧,我说不累,给你按一会,我的手臂也会轻松,要不,我也僵住了,我又在和他开玩笑了。(他知道,我是类风湿,不运动关节就僵了)于是,他闭上眼睛,静静休息。
大约五分多钟,他就说,扶我起来,我说多躺一会吧,他说不行,有点胸闷,起来坐会,打会坐。 他说打会坐,一吸三呼,做会深呼吸,胸闷就会缓解。这是翟丽新前几年教我的,我也占这个光了。我说,你真行,久病成医了。我又在打趣。此时,我的脸在笑,可心在哭,在疼,在滴血………
一个连五分钟都不能躺下来好好休息的人,他忍受的会是怎样痛苦呢……
那天下午我们还谈到了艺术馆开馆的事情,他说抓紧点,争取七月份开馆,我也出去给朋友们见个面。我说没问题,你放心吧!
因为这段时间为了让大师好好休养,关掉了手机,有些朋友打电话不通,就打到了我这里,如占良、庆华老弟,巧玥大姐,北京的李树喜老师等好多好朋友,都说要来看他,他都让我一一谢绝了。他说到时候一定把这些好朋友们都请过来。
看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信心的。
第一时间,得到了大师离开的消息,没来的及换正装就赶了过去(正好我也在保定。)摸一摸他的手溫热溫热的,看一看他的脸即平静又安详。也许他走的并不痛苦,并不纠结,可是他不该走啊!他还这样年轻!我使劲摇着他的肩膀,哭着,喊着,文增,文增,你这是干什么呀?说好了艺术馆开馆仪式上出来,你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我们的人生路才刚刚走了一半,你怎么就突然不走了呢?你这是干么,你这是干什么呀………天啊………我的天啊………………
注:文中图片是2015年9月份在曲阳白家湾公园照的,因身体不好和劳累过渡,面容已明显苍老,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学生杨丽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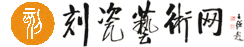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
鲁公网安备 37039002000142号